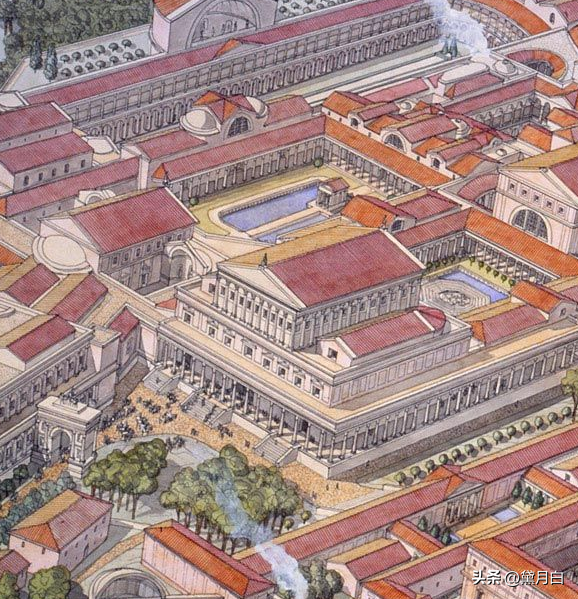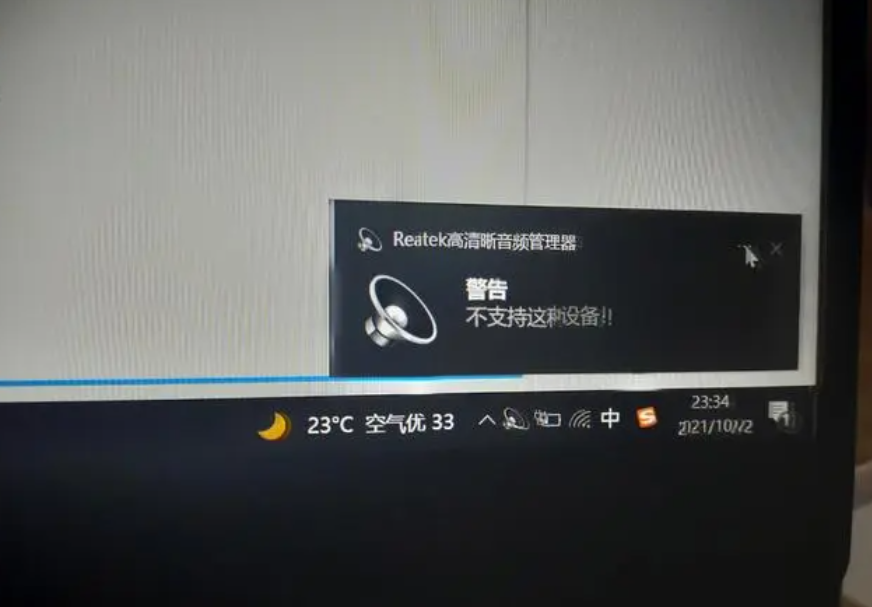东南欧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定义
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通常被理解为相互排斥的意识,在东南欧史学中,帝国经常被描述为“国家的监狱”,注定要崩溃,让位于“真正的”民族国家。
民族运动经常被认为是在破坏帝国秩序和建立民族国家方面可以发挥核心作用。
最近的许多研究人员都对这些假设提出了质疑,许多历史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已经证明,其中最出名有贾德森 、库马尔 、马莱舍维奇、斯蒂芬诺夫 、斯特加和舍尔等人。

通过解释帝国如何经常在不知不觉中促进民族主义扩散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结构的发展,成功地解构了对哈布斯堡王朝晚期和奥斯曼帝国的传统理解。
这些研究令人信服地表明,19世纪和 20 世界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并非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而是经常共存并相互加强。
随着研究的进步,研究人员通过质疑传统的史学范式来进一步推动分析,不仅质疑“大众渴望”民族独立的传统史学范式,而且质疑主导最近分析的有影响力的“民族冷漠”概念。
更具体地说,奥匈帝国结构在19世纪后期不满情绪同质化中的作用和 20世纪初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帝国国家没有扼杀所谓的充满活力的民族认同,也没有在普遍的民族冷漠中运作,而是在形成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现实理解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并能说哈布斯堡王朝政府在虚无中制造了民族主义抵抗,相反,不满情绪的国有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奥匈帝国不平衡和日益强制性政策的意外后果。
研究人员支持奥匈帝国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统治的强制性、意识形态和微观互动力量之间的脱节,大大促进了不同形式的抵抗同质化。
传统的欧洲史学经常描绘19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民族主义的鼎盛时期,在这种传统叙事中,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带头瓦解了帝国秩序,并以这种方式满足了普通民众生活在自己主权和独立民族国家的普遍愿望。
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和罗曼诺夫帝国的崩溃,经常通过崛起和不妥协的民族主义者的棱镜来解释,他们挑战并最终推翻了这些帝国的“国家监狱”。

甚至一些极具影响力的当代民族主义学者,如威默和赫罗克也坚持认为民族主义领导人和民族主义运动导致了帝国秩序的崩溃。
他们挑战了对自己民族国家的“大众渴望”的传统说法,但他们仍然将民族主义视为帝国垮台的主要触发因素。
对于威默来说,“民族主义者创造了民族国家,无论国家是否已经建立”,而赫罗克认为民族运动锻造了现代国家,因为它们受到民族主义梦想和希望形式的人类意图驱动。
作者认为:这些方法与传统的史学强调相同,强调在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在这种理解中,重点是民族主义鼓动者,他们成功地动员了民众支持反对帝国统治。
传统的史学倾向于以国家的长期观点运作,认为国家一直存在,只需要“唤醒”,当代民族主义学者,如威默和赫罗克很清楚国家是一种现代现象,在他们的解释中,民族主义运动需要改变公众的看法,将普通人转变为具有民族意识的公民。

这种根深蒂固的观点最近受到一些历史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的质疑,他们认为帝国世界的崩溃不是由想要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和普通个人造成的。
这些学者指出,帝国崩溃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偶然的,政治变化、战争、革命、经济崩溃和各种其他社会因素的结果。
这些新的研究表明,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有争议的过程,它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在独立政体建立之前而是之后开始的。
新政体的人口只有在这些事件发生后才被国有化,而不是受到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或明确定义的民族主义计划驱使,最后导致帝国崩溃,而是“国家的行动实际上创造了以前不存在的民族主义运动”,在许多情况下,帝国本身在不知不觉中为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出现创造了空间。
研究人员发现这些方法同样挑战了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对国家形成的描述。

他们表明,在19世纪,民族注定不会成为现代国家,正如史密斯和阿姆斯特朗所论证的那样,另一方面,扎拉和贾德森表明,盖尔纳安德森和霍布斯巴姆在内对古典的民族主义理论不够敏感,无法解释国家形成。
因此民族的漠不关心并不是缺乏种族核心的标志,相反,正如扎拉和贾德森所认为的那样,与其说是民族冷漠的残余,不如说是现代性的产物。
用扎拉的话来说,“这个想象中的非社区,通过民族主义者自己不断努力,变得栩栩如生并制度化”。
所以民族冷漠的出现,是对19世纪欧洲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政治现实的回应,这不是“政治参与的二元对立面,反映了大众的无知或前现代遗物”,而是“对现代大众政治的回应”。

新观点成功地挑战了传统和当代对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描述,他们让人相信,在帝国的崩溃和民族国家的建立中,没有什么是自动的、不可避免的和不可逆转的。
它们还表明,集体和个人依恋具有高度的可塑性,情境性,并且可以采取非常多样化的形式。
国家地位从来不是一个目的论的发展,而是一个偶然的、不可预测的、可逆转的过程,其特征是社会不平衡、历史动荡和多方面的转变。

帝国结构的崩溃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在19世纪后期和 20世纪初期的欧洲,与民族主义鼓动者的野心和普通民众的民族愿望关系不大,而是与相互竞争的社会组织如帝国、秘密社团、叛乱组织、社会运动和其他有组织实体的强制组织能力和意识形态渗透有关。
作者认为:民族主义和非国家话语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组织、意识形态和微观互动能力。
现代帝国和民族国家都拥有相当大的强制性组织能力,并且能够有效地在意识形态上渗透到它们所控制的社会中,它们在微观互动能力方面通常有所不同:民族国家通常能够成功地包裹微观层面的团结网络,而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帝国通常无法完全渗透微观世界。

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政体形式战胜了帝国结构,并逐渐成为领土统治的唯一合法形式,在这种背景下,民族主义也取代了帝国主义,成为当代世界最有力、最受欢迎的全社会意识形态话语。
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也共存并相互加强,他们还受到许多其他意识形态项目的挑战,此外,以民族为中心的身份类别形成和扩散并不是国家的专属特权,除了自上而下的发展之外,国家分类还通过其他社会组织发展,包括宗教机构、私营公司、政党和其他在民间社会范围内工作的团体。
一旦民族国家模式在全球层面获得霸权地位,帝国主义就会被剥夺合法性,从20世纪下半期开始,没有一个政体依靠帝国学说来证明其存在。
虽然现在很清楚这种大规模的转变是在过去两个半世纪中发生的,但不太清楚这一历史过程是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日常生活中展开的。为了捕捉这一过程,研究人员放大了哈布斯堡王朝及其挑战者,在1878年至1918年间重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意识形态格局中的作用。

研究人员重点讨论了定义欧洲这一地区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历史轨迹的三个关键过程,分析了相互竞争的强制性组织、意识形态和微观互动力量如何塑造了帝国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及为什么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和政治现实理解最终获胜。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人员探讨了帝国国家的强制组织、意识形态和微观互动权力的作用及其对普通民众的影响。
强制组织能力的特点是一个人能够成功地指导和协调人员、资源、沟通、交通以及各种其他社会角色和服务的能力。
这一过程需要纪律能力和使用胁迫手段来实现既定目标,强制组织能力的定义特征是有效的分工、明确阐述的等级指挥链、一定程度的精英社会流动性、遵守规则以及对组织的忠诚和服从的期望。

意识形态的力量植根于规范性守则和原则,这些规范和原则为现有的社会组织及其行动辩护,在复杂的社会组织都不能仅通过胁迫来运作,因此它们设计和使用特定的意识形态来使其所做的事情以及它们存在的合法化。
随着强制组织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意识形态也随着它能够利用新的和改进的基础设施能力而扩大,例如:交通、通信和管理的发展最终影响了方言的标准化,识字率的大幅提高和人口的文化同质化。
这些变化促进了公共领域、义务教育、大众媒体等,这些领域在意识形态叙事的扩散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随着强制组织能力的提高,意识形态渗透得到加强,并能够遍及整个社会和政治秩序。
最后,微观互动能力也塑造了普通人的信念和行为,人类是以意义为导向的生物,他们在小而亲密的群体情感和道德的依恋中茁壮成长,他们的大部分行为都受到这个微观世界复杂性的支配,换句话说,大多数人都嵌入到微观层面的团结网络中,在那里他们与亲密的家庭成员、亲属团体、恋人、亲密朋友和同龄人群体建立了牢固的联系。
作者认为:非国家组织的能力和国家的组织能力差异犹如天差地别
从历史上看,国家往往比非国家组织拥有更多的强制性组织和意识形态能力,从原始的城邦到世袭王国、帝国和其他形式的政体,国家权力传统上由中央集权、等级分工、军事、司法和行政控制来定义。
国家和非国家之间的这种差异与民族主义息息相关,首先,由于国家拥有更大的强制性组织和意识形态能力,它们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内制度化和传播民族主义思想。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